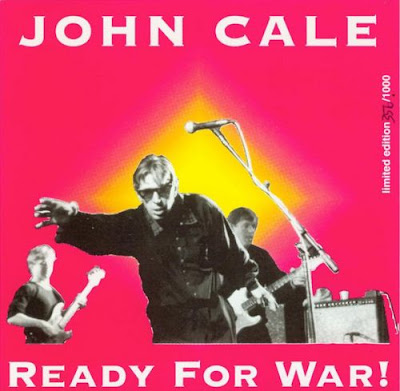轉載自http://corenna.blogbus.com/logs/2828551.html
噪音的文化隱喻
張傑
摘要:噪音在現代社會中的出現頻率越來越高,並因此形成一種有文化意味的現象。文章首先運用詞源考證法,考察噪音的最初能指,然後從作家或思想家們對噪音的態度和噪音音樂出發思考了噪音的兩種本原意義,進而從《白噪音》、《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等文本中發掘出噪音的多樣文化隱喻。文章最後表明對噪音所具文化隱喻的態度。
關鍵字:噪音;能指;所指;隱喻
噪音並非自工業革命後方才產生,從一般意義上理解,任何對他人的生活、學習或工作構成妨礙的聲音就是噪音。普通人解決的辦法無非是以口頭或動作表示抗議並努力消除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噪音在現代社會被描述為一種污染,可與工業、交通、建築等污染相提並論,而且被以法律和資料的形式嚴加規範。國家專門制定《環境雜訊污染防治法》,把超過規定的環境雜訊排放標準並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現象,稱為環境雜訊污染。
如今,“噪音”一詞在生活中的出現頻率越來越高,足見其在現代社會中的深刻影響。本文意圖從追溯噪音的起源開始,對“噪音”的能指和所指作一粗淺的探索。
一
《說文解字》中,噪,擾也,從一開始,噪音就表示對別人的擾亂。此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過,當時的“噪”寫作“譟”,可見更多的是指言語對別人的擾亂。後來,能指逐漸拓寬,諸如車聲,鼾聲,流水聲,動物的鳴叫,等等,只要對他人構成一定程度的干擾,就可以稱為噪音。人們可以比較自由地以睜眼或閉眼來表明自己對某事物的關注或排斥,正所謂一葉障目就能不見泰山,可忍受噪音對很多人來說卻是萬般無奈和被迫的,語音的穿透力和耳膜的脆弱性、暴露性使我們在喧囂吵鬧前非常被動。叔本華一本正經地說假如大自然打算叫人思考問題,她就不應當賜予他雙耳;或者,至少應當讓他長出一副嚴密的垂翼,就像蝙蝠所具有的那令人羡慕的雙翼一樣。他對人擁有耳朵耿耿於懷,“無論白天還是黑夜,他都必需始終豎張著雙耳以保持警惕,提醒自己注意追蹤者的接近。”[1]他本人深諳噪音之苦,認為噪音是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東西,為此他不惜把一個製造噪音的女房客推下樓梯,結果為此承擔了三十年的贍養責任。他還將對噪音的厭惡寫成文章《論噪音》,編入他的論文集,在這篇奇文中他尤其談到鞭聲給他帶來的痛苦,“沒有比那可詛咒的鞭打更強烈的刺激了,你會感到那鞭打的疼痛簡直就在你的頭腦中,它對大腦的影響如同觸摸一棵含羞草那樣敏感,並在持續時間的長短上也是相同的。”在馬鞭的抽打聲中,叔本華覺得自己的思路越來越困難,“仿佛兩腿負重而試圖行走那樣困難”,因此他對噪音簡直是深惡痛絕,認為“在各種形式的紛擾中,最為要不得的要數噪音”[2]。
與叔本華極為相似的是卡夫卡,後者以小說的形式控訴了噪音的折磨。如他的《巨大的吵鬧聲》,“在此以前我就想到,現在我聽見金絲雀的叫聲我重又想起,我是否該把門打開一條縫,像蛇那樣爬進隔壁房間,蹲到地上,向我的妹妹們和她們的保姆請求安靜。”[3]比起叔本華來,卡夫卡對噪音的態度顯得軟弱無力。他認為唯有在安靜中創作才會得到身體和靈魂的雙重解放,他幻想最理想的寫作地點“在一個大的被隔離的地窖的最裏面。有人給我送飯,飯只需放在距我房間很遠的地窖最外層的門邊。我穿著睡衣,穿過一道道地窖拱頂去取飯的過程就是我唯一的散步。……那時我將會寫出些什麼來!我會從怎樣的深處將它們挖掘出來,毫不費勁!”[4]。儘管如此,他卻幾乎大半生時間都與父母同住,沒有主動避開家人製造的噪音。他對噪音表示的最大反抗就是對婚姻總是猶豫和反悔,雖然噪音並非他恐懼婚姻的唯一因素。
這種對噪音的深惡痛絕常人似乎難以接受,叔本華、卡夫卡等往往被認為有些病態和極端,人們甚至猜想這可能與他們的神經類型和身體狀況有關。但作家們並不買帳,餘光中憤然寫道“噪音害人于無形,有時甚於刀槍。噪音,是聽覺的污染,是耳朵吃進去的毒藥。”他認為,一切思索的或要放鬆休息的人都應該有寧靜的權利。因而,當社會不能給人提供安靜的生活空間時,一定是這個社會哪邊出了什麼問題。所以他提出“愈是進步的社會,愈是安靜。濫用擴音器逼人聽噪音的社會,不是落後,便是集權。”[5]由此,有無噪音上升為衡量社會進步與否的一個重要尺度,這就比叔本華和卡夫卡看得更具普泛的社會意義。後兩者只是把噪音視為個人寫作的干擾,叔本華更是從自我思考受阻的角度,指控噪音是那些精力體力過剩的人製造出來的,他甚至寫道:“我長期有這種看法,一個人能安靜地忍受噪音的程度同他的智力成反比,因此它可以看作衡量一個人的智力的很公正的尺度。……噪音對所有聰明人都是一種折磨。……用敲打、錘擊、摔四周的東西等形式來顯示過剩的生命力,都是我一生中天天必須經受的折磨。”[6]更甚之,他認為噪音“是一種純然放肆的行為”,“甚至可以說是體力勞動階層向腦力勞動階層的公然蔑視”[7],因此,叔本華以噪音劃分兩種勞動者的界限,並顯而易見地給出高下之分,其意圖在於彰顯思考和思考者的重要性,這與孟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邏輯基本相同。叔本華還想當然地認為普通勞動者不會對噪音有什麼反應,因為他們不會思考,他們的大腦組織太粗糙。與卡夫卡隊寫作環境的幻想不同,他幻想的是假如生活於這個世界上的都是些真正有思想的人,那麼,各種噪音就不會如此肆無忌憚地擾亂世界的寧靜而無人制止了,這就有點像尼采的“超人”論了。卡夫卡雖強調寫作狀態,倒並沒有去刻意較量寫作與別種勞動的高下,也並沒有質疑勞動人群的生存理由,他更重視的是面對寫作個體生命的全然坦誠和投入。
當然,三者的共同點更明顯,都深刻地覺察到了噪音的危害,並呼喚對寫作者思考者的尊重,進而我們可以將之上升到呼籲對每一個人的尊重,這種尊重而且是與社會公民素質的提升成正比的。
其實,噪音不僅對知識份子,對普通人也類乎一種苦刑。現代工業和後工業的發展使噪音成為人體生命日難承受的污染,商場、超市、大街、建築、交通等無不是噪音的主要製造者。電影《青春無悔》中有這樣的情節:臥室外是無處不在的興建工程的噪音,主人公加農拿出一條細布繩緊緊綁在頭上以抗拒噪音帶來的頭痛。製作者將都市現代化給人們生活與文化造成的副作用以身體傷害——腦癌的形式呈現,寓意深遠,而主人公的父親告訴兒子忘記頭疼的辦法是更努力地工作,以噪音來對抗噪音,這顯然是十分反諷的。更為反諷的是,加農是負責拆舊房的——他既是受害者,又是都市的象徵和現代化的推動者。
噪音的高殺傷性的確不容忽視,因此能用作武器來對付他人。電視劇《西遊記》中有一集“觀燈金平府”,唐僧被三個犀牛精擄到青龍山,孫悟空單憑武功能打敗三個妖精,但是當眾多小妖圍成一圈沖著他狂叫,他卻敗出圈外,直到後來在耳中塞進棉花球方才打死小妖。還有一次是在女兒國遭遇琵琶精,後者一彈琵琶,孫悟空的腦袋就像被狠狠地蜇了一下,同樣因忍耐不得敗去。不過更可怕的是用噪音來逼供,將人關在鎖音效果極好的有高音喇叭的封閉房間裏,不斷播放噪音,四面的牆壁經過特殊處理還可以增大回音,這種懲罰不像毒打、夾手、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直接傷及肉體,但囚犯卻往往能很快招供,忍耐不住這種特殊處理的噪音對神經的殘酷折磨。
還是在《你的耳朵特別名貴?》一文中,余光中先生說,人叫狗吠,到底還是以血肉之軀搖舌鼓肺製造出來的“原音”,無論怎麼吵人,總還有個極限,但是用機器來吵人,收音機、電視機、唱機、擴音器、洗衣機、微波爐、電腦,或是工廠開工,汽車發動,這卻是以逸待勞、以物役人的按鈕戰爭,而且似乎是永無休止沒有終結的——技術時代的人們必定要為享用技術付出代價:必須忍受馬路上高分貝的吵鬧,忍受狹隘的公共空間中的嘈雜,忍受電子產品雖微弱但執著的振動聲,而安靜,在今日都市卻日漸轉成上層人士和中產階層的特權,成為其社會地位和經濟能力的證明。魯迅《幸福的家庭》中的“他”,想通過寫小說來緩解窘迫的家境,他一邊努力虛構一個幸福家庭,一邊頻頻被妻子買菜和買劈柴的噪音拉回現實生活,最後不得不承認個性解放和生命自由的烏托邦破滅,不得不“俯首甘為稻粱謀”,其中噪音既諷刺性地提醒了小說中的人物,又昭顯了其窘迫的生存境況。
但人們也有喜愛噪音的時候,這表現在兩種情況中,一是自己並不需要安靜時自己發出噪音,此時是不管他人如何的,這也就是余光中先生深為之擔憂的公民素質和社會進步問題;另一種是全民狂歡,比如放鞭炮,人們對鞭炮聲大多並不表示反感,相反,多年嚴禁之後的限放政策讓很多人歡呼,不少居民不惜為之花費數千元,因此說是限放,實際上成了全放。更有專家來辯護“一刀切的禁放政策,使得傳統節日味道越來越淡,不僅令傳統節日日漸式微,阻礙了傳統文化的承繼和復興,而且使得辛勞了整整一年的公眾,其新春時節的快樂感和幸福感大打折扣”[8],爆竹越響似乎表示放爆竹者心情越暢快,財力越雄厚,但熱鬧顯然並不必然是繁榮穩定幸福的同義語。不過從人們的笑臉上可以看出,鞭炮製造的噪音在國人的意識裏一直代表著喜慶和熱情。
二
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噪音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即音高和音強變化混亂、聽起來不諧和的聲音,由發音體不規則的振動而產生,與之相對的樂音自然就是有一定頻率,聽起來比較和諧悅耳的聲音,由發音體有規律的振動而產生。這是在嚴格的音樂意義上的比較。
20世紀以前的傳統音樂審美原則規定了樂音是組成音樂的基本語彙,但進入20世紀後,音樂創作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代主義對傳統幾乎作了全盤否定。1913年,義大利未來主義作曲家盧梭洛發表《噪音的藝術》,主張將噪音用作音樂作品的基本音響材料,以表現現代機械文明,並為此創作了由震動聲、軋軋聲、口哨聲等組成的噪音音樂作品。如同工業進入了繪畫一樣,噪音從此進入了音樂,比如“商店中金屬屏風的墜地聲,門砰然一聲關上的聲音,人群的喧嘩聲,各種各樣從車站、鐵路、鑄鐵廠、紡紗廠、印刷廠、發電廠與地鐵傳來的嘈雜聲,以及全新的現代戰爭的噪音”,甚至包括撕紙聲,咳嗽聲,腳步聲,等等。噪音音樂企圖告訴人們:在無限豐富的音響世界中,被作曲家用來建立音調體系的只是一小部分,生活中還有許許多多可供採用的音響材料,甚至一切聲音都可入樂。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倒頗合乎《禮記•樂記》中所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幹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9]既然噪音也是現實事物造成的聲響,當然也能夠進入音樂的殿堂了。看似簡單的噪音加入,實際上,音樂的傳統定位就被深刻地改變了。早在兩千多年前柏拉圖就對音樂下結論說“和諧是永存的”,畢達格拉斯學派堅持音樂是對立因素的和諧的統一,把雜多導致統一,把不協調導致協調,甚至認為淨化靈魂的方法唯有音樂。老子也有言“音聲相和”,音者,樂音是也;聲者,雜訊是也。所謂“大音希聲”,大音者,不使雜訊過度喧囂之美音是也。從形式美的觀點看來,他們都認為音樂應該是優美的,就像春風微雨,嬌鶯嫩柳般溫和自然、舒緩靜態、輕盈流暢,使人得到平靜的愉悅。中國傳統音樂更是形成了“中和”的音樂審美原則:平和、恬淡,溫柔敦厚。如今,噪音介入甚至在有時佔據全章,自然使音樂顯得不那麼和諧了,由此引發了什麼是音樂美和如何鑒賞噪音音樂的爭論,最為激烈的怕是表現在對搖滾的爭執上。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美國搖滾遭到了猛烈攻擊,一些醫生從生理角度出發表達對搖滾的排斥,其理由是,搖滾樂高至110~119分貝的大音量嚴重超出聯邦政府制定的噪音標準,這種噪音比工業噪音還危險,還具破壞性,必將對人的內耳造成創傷,而且隨著揚聲器的輸出功率從60年代末的1000瓦發展到70年代中後期的近萬瓦,一些搖滾樂隊被指責為根本不是在演出,而是在製造電閃雷鳴。但是,隨後的研究發現,這些醫生的論斷並不科學,因為身處其中的搖滾樂手聽力並沒有明顯的破壞,因此又有醫生指出,噪音是否會對人的聽力造成損害取決於那種聲音對聽者構成的壓力大小,所以,如果聽者討厭搖滾,聽力可能受損,而如果是帶著興趣去欣賞,並視噪音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部分,聽力就不會受損[10]。
的確,對噪音音樂如何欣賞和評價是我們是否接受它的關鍵。旅美華人作曲家和電子媒體藝術家姚大鈞說:“人們剛接觸的時候會覺得一團混亂,沒有脈絡可循,仿佛隨便怎樣亂搞都可以搞出一套自圓其說的東西。其實,批評、解釋的法則與傳統音樂是一樣的。如果你要表達一種情緒,還是需要一定的技術,雖然是在用一種表面混亂的形式表達,但如果技巧不夠,一聽就能聽出來。”也就是說,搖滾等噪音音樂並非像一般人所說的那樣混亂不堪,傳統音樂的闡釋規則也可以運用。姚大鈞還寫過一篇《噪音聽法論》,序言裏說:“一般聽噪音音樂的方法,多半是讓自己完全臣服於這類作品中,以被虐狂式的心態讓高分貝的聲音海完全淹沒自己,並一定堅持到最後一秒鐘。”[11]
有很多像姚大鈞這樣的音樂人認為噪音在音樂中被重新賦予了生命,它激發著人的聽覺神經,將一份狂熱的感情推向極點,從目前搖滾在群眾中尤其是青少年中的普及程度來講,至少噪音音樂在一定範圍內已被認可,更有人將其上升為噪音美學,這一點還尚待專業人士確認。不容忽視的一點是,搖滾的噪音借助了現代技術(如大規模複製,高分貝播放手段,電吉他,電子合成,採樣拼貼,噪音實驗等)的東風。在流行音樂和搖滾的狂舞轟鳴中,古典的“天籟”(包括旋律、節奏與和聲)受到了衝擊,莊子所說的“動則失位,靜乃自得”也被擠到了舞臺上的最邊角。
三
從前兩部分來看,噪音無非有兩種能指,一指生活中刺耳的聲音,一指音樂中迥異於和聲的語言組成材料,但是,詞語的能指和所指往往是不等同的,“噪音”這個普通的詞語在當代也逐漸具備了新的文化隱喻。對隱喻德國哲學家凱西爾是這樣界定的:
“有意識地以彼思想內容的名稱指代此思想內容,只要彼思想內容在某個方面相似於此思想內容,或多少與之類似。”
他把隱喻視為“以一個觀念迂回地表述另一個觀念的方法”,簡單地說,隱喻就是以源域中的一個概念去解釋目標域中的一個概念,解釋是建立在二者的相似性或類似性基礎上的[12]。
美國作家唐•德里羅於1985年發表小說《白噪音》,該書之出名不僅在於它較為奇怪的標題,更在於標題本身揭示和象徵的蘊涵。作者自己是這樣解釋的,“關於小說標題:此間有一種可以產生白噪音的設備,能夠發出全頻率的嗡嗡聲,用以保護人不受諸如街頭吵嚷和飛機轟鳴等令人分心和討厭的聲音的干擾或傷害。這些聲音,如小說人物所說,是‘始終如一和白色的’。傑克和其他一些人物,將此現象與死亡經驗相聯繫。也許,這是萬物處於完美平衡的一種狀態。”這樣的解釋本身也難懂,作者接著又說,“白噪音也泛指一切聽不見的(或‘白色的’)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淹沒書中人物的其他各類聲音——無線電、電視、微波、超聲波器具等發出的噪音。”[13]這樣,我們就可以借用美國學者科納爾•邦卡所說,將現代科技產物的商品所發出的噪音均可稱為“消費文化的白噪音”,這是伴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自身釀制的苦果”。這一類白噪音,在小說中具體表現為電視和無線電廣播的各種節目,喋喋不休的廣告,超市和商城裏交易時人類的嗡嗡聲,甚至包括旅遊景點“美國照相之最的農舍”周圍照相機快門不停的喀擦聲。
如果白噪音的寓意僅止於此的話,那文章的這一部分完全可以併入第一部分,但是作者顯然要賦予白噪音更特別的隱喻。書中主人公傑克和妻子芭比特有這樣一段對話:
“沒有人看出來,昨夜、今晨,我們是何等的害怕——這是怎麼回事?它是否就是我們共同商定互相隱瞞的東西?或者,我們是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心懷同樣的秘密?戴著同樣的偽裝。”
“假如死亡只不過是聲音,那會怎麼樣?”
“電噪音。”
“你一直聽得見它。四周全是聲音。多麼可怕。”
“始終如一,白色的。”
“有時候它掠過我。”她說,“有時候它一點點地滲入我的頭腦。我試圖對它說話:‘現在不要,死神。”[14]
白噪音因此與人的死亡體驗緊密相關,掩藏著人對死亡的所有恐懼和想像。書中更精妙的一點還在其後,另一個小說人物默里把傑克的死亡恐懼看成是不自然的,正像他認為“閃電和雷鳴是不自然的”,他說傑克不知道怎樣自我壓抑,而在他看來,“我們自我壓抑、妥協和偽裝”方才是“我們如何倖存於宇宙之中的方式”,這種壓抑、妥協和偽裝就是“人類的自然語言”[15]。自然與非自然在小說中的所指已截然相反,所以白噪音除了作為物質社會的渣滓,最深切地表述了當代人對於死亡的恐懼,所有的經壓抑、妥協和偽裝而表現出來的白噪音還被認為表現出“人類交流死亡恐懼的努力和驅逐它的欲望”[16],如孩子長達七小時的無來由的哭泣,睡夢中發出的神秘聲音,修女們在根本不信任上帝和天堂的情況下日復一日的宗教說教,這些噪音在對抗死亡上達成一致。白噪音因此最終成為人類拒絕死亡的自然語言,真是莫大的反諷!
再回到我們第一部分談到的電影《青春無悔》,雖然噪音構成了對加農生命的威脅,但是如果沒有噪音,加農又能憑什麼居住在高樓大廈裏?噪音既是毀害生命的殺手,又是現代人生存不可或缺的依靠,甚或可以說,噪音在某種意義上隱喻著現代物質社會的蓬勃發展。
如果說白噪音還是從最普遍的社會生活角度,那麼法國人賈克•阿達利的《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就是從政治和經濟學意義對噪音作了耳目一新的闡釋,在此我們只談政治意義。他首先認為“不是色彩和形式,而是聲音和對它們的編排塑成了社會”,因此音樂與政治的關係更緊密,“與音樂同生的是權力以及與它相對的顛覆”,而與噪音同生的是混亂和與之相對的世界。在噪音裏我們可讀出生命的符碼、人際關係、喧囂、旋律、不和諧、和諧;當人以特殊工具塑成噪音,當噪音入侵人類的時間,當噪音變成聲音之時,它成為目的與權勢之源,也是夢想——音樂之源。它是美學漸進合理化的核心,也是殘留的非理性的庇護所;它是權力的工具和娛樂的形式[17]。噪音就是不和諧,就是異質和權力爭奪的化身。
上述闡述恰恰為“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18]作了現代注解,“怨”再上加“怒”顯然違背了“中和”的傳統音樂審美觀,因此可以說噪音產生於混亂和同樣混亂的世界中,或者說噪音就是亂世的徵兆。搖滾裹挾著沉重的音響設備,吼著電閃雷鳴般銳利至極的聲音,希望借此刺激青年使他們“從麻木不仁之中驚醒” [19],使他們意識到民主平等和平自由在當代現實理性社會中的匱乏,很多樂人包括中國的郝舫、崔健等人都一直是以這種觀點來欣賞和從事搖滾事業的,搖滾遭到以民主自詡的社會主流不遺餘力的攻擊在他們看來正是搖滾所寓政治意義的顯現。
在專制極權時代,一些往常被視為異類的事物會被藝術家們用來遙托寓旨,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穆旦在1975年曾寫下一首短詩《蒼蠅》,“你永遠這麼好奇/生活著/快樂地飛翔/半饑半飽/活躍無比/東聞一聞/西看一看/也不管人們的厭膩/我們掩鼻的地方/對你有香甜的蜜/自居為平等的生命/你也來歌唱夏季/是一種幻覺/理想/把你吸引到這裏/飛進門/又爬進窗/來承受猛烈的拍擊”。蒼蠅這種製造噪音人皆厭惡的害蟲,在穆旦的筆下化為充滿理想色彩的追求平等者,最後被設下騙局使詐的人們所害。還有瘋狗(食指)、野獸(黃翔)、華南虎(牛漢),等等,它們發出的呼叫就成為抗爭那個淒冷壓抑時代的噪音。這個時候,沈默不再是金,高呼方顯英雄本色,所以1968年的“五月風暴”才永遠為世人感懷,沈默在彼時被視為無能和軟弱。
既然任何聲音就政治意義而言都是“權力的附屬物”和工具,面對這樣的噪音,極權主義者的回答必然是“查禁顛覆性的噪音是必需的,因為它代表對文化自主的要求、對差異與邊緣游離的支持”,阿達利指出,這種對維護音樂主調、主旋律的關切,對新的語言、符號或工具的不信任,對異於常態者的擯斥,存在於所有類似的政權中。所以,才會有了食指的瘋癲,黃翔的早逝,索爾仁尼琴的流浪,搖滾的被抑……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借鑒福柯對權力的闡述來為噪音作一全面的界定。福柯認為,權力是“自下而上”的,大量的權力關係和權力形式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橫斷面,存在於各種各樣的差異中,存在於任何差異性的兩點中,並“在各種不均等和流動的關係的相互作用中來實施”[20],那麼,既然噪音也是無處不在的,而且因一方的聲音高出或異于另一方而形成,我們同樣可以說,噪音存在於各種各樣的差異中,存在於任何差異性的兩點中,只要有差異,就會有噪音,就會產生對噪音的壓制和規訓。如此說來,任何超出常規具有異質色彩的事物均可構成噪音,尼采,凡高,《沉淪》,《呐喊》,《嚎叫》,貓王,《回答》,《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無所有》,等等。
但是噪音絕對地有政治意義嗎?賈克•阿達利的論述和《禮記•樂記》分明向我們指出了這一點。可眾聲喧嘩究竟徵兆著民主的福音還是無序的混亂?還有噪音音樂的形式和它希望表達的內容統一嗎?越震耳欲聾就越能完好地宣洩對社會的不滿嗎?稽康在一千多年前就提出“聲無哀樂論”,反對從倫理觀、功能論出發去衡量音樂的美,所以搖滾的反叛從這一點來看又很值得質疑,倒是它的登峰造極的噪音有時的確讓人忍無可忍。德國美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肯定地說“這些前衛派的實驗無以作為人類聽覺設計的指導方針,無以成為一種聽覺環境倫理學的指導方針。”[21]文章先後闡述了噪音的原始能指和新的文化隱喻,可以看到,
對噪音的厭惡,以及加諸噪音之上的那些隱喻,不過反映了我們的諸多不足:對安靜的強烈渴望,對現代化盲目崇拜造成的魯莽,對快節奏變化的焦慮和猶豫,對平庸的逃避,對自我和現實的不滿,還有我們在構建一個理想社會時不斷湧上的無力感。耳對噪音,灰色人群聽而不聞顯得滯鈍,他們更緊要的是去滿足基本生存需要,像叔本華所說的他們可能根本不需要作什麼抽象思考根本不擔心被打擾;中產階層則正力圖營構一個個愈發舒適的空間,向著心儀已久的上流社會直奔,自有隔離網使他們遠離一切噪音。在噪音中適應噪音,乃至忘卻噪音,築起“心齋”,恐怕是這個時代最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只是,人世的喧嘩與浮動,我們能完全躲得開嗎?即使躲得過,聰,察也,這樣的人還稱得上“聰”嗎?我還是願意這樣憧憬:一個平和理想的社會將很快出現,它將解決噪音以如此多樣和複雜的隱喻所反映出來的全部問題,每個人都將獲得思考和言語的權力與表達空間,噪音將被化解於無形。
The Cultural Metaphor of Noise
Abstract:There is a word which is getting a higher appearing frequency and one kind of cultural phenomenon thus comes into being. It is Nois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noise’s original signal, then analyzes it’s two fundamental meanings from noise music and the writers’ or thinkers’ attitude to noise, and then unearths the multiple cultural metaphors of noise from White Noise, Noise:Political economics of Music ,etc.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expresses her attitude to these cultural metaphors of noise, expecting that a perfect society will appear and all the problems indicated by these metaphors of noise will get solved.
Key words:Noise;Signal;Signification;Metaphor
參考文獻:
[1]【德】叔本華. 論獨思..叔本華論說文集[M].範進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355.
[2]【德】】叔本華. 論噪音.叔本華論說文集[M]. 範進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492-493.
[3]【奧】卡夫卡. 卡夫卡短篇小說全集[M].葉廷芳主編. 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 211.
[4]【奧】卡夫卡. 致菲利斯情書.卡夫卡全集(第9卷)[M]. 葉廷芳主編. 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213.
[5]餘光中. 你的耳朵特別名貴?[EB/OL].http://ww.chineseliterature.com.cn/xiandai/ygz-wj/021.htm,2006-07-01.
[6]叔本華:遲到的榮譽[EB/OL].http://www.grassy.org/Star/FPRec.asp?FPID=5683&RecID=3,2002-03-03.
[7]【德】叔本華. 論噪音. 叔本華論說文集[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494.
[8]湯萬君. 管理公共事務要勇於面對麻煩——從北京市煙花爆竹燃放“禁改限”說起[N]. 南方週末,2006-02-16(1).
[9]張文修. 禮記•樂記.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254.
[11]李宏宇. 北京聲納:用噪音做音樂[EB/OL].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1120/wh/dyyy/200311200876.asp,2003-11-20.
[12]【德】恩斯特•凱西爾. 語言與神話[M].於曉等譯. 北京:三聯書店,1988. 105.
[13]【美】唐•德里羅. 唐•德里羅致譯者信.白噪音[M]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1.
[14]【美】唐•德里羅. 白噪音[M].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217.
[15]朱葉. 美國後現代社會的“死亡之書”(譯序).【美】唐•德里羅.白噪音[M].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3.
[16]朱葉. 美國後現代社會的“死亡之書”(譯序).【美】唐•德里羅.白噪音[M].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3.
[17]【法】賈克•阿達利. 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M].宋素鳳、翁桂堂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
[18]張文修. 禮記•樂記.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255.
[19]郝舫. 傷花怒放——搖滾的被縛與抗爭[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296.
[20]汪民安. 福柯的界限[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218.
[21] 【德】沃爾夫岡•韋爾施. 重構美學[M].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189.